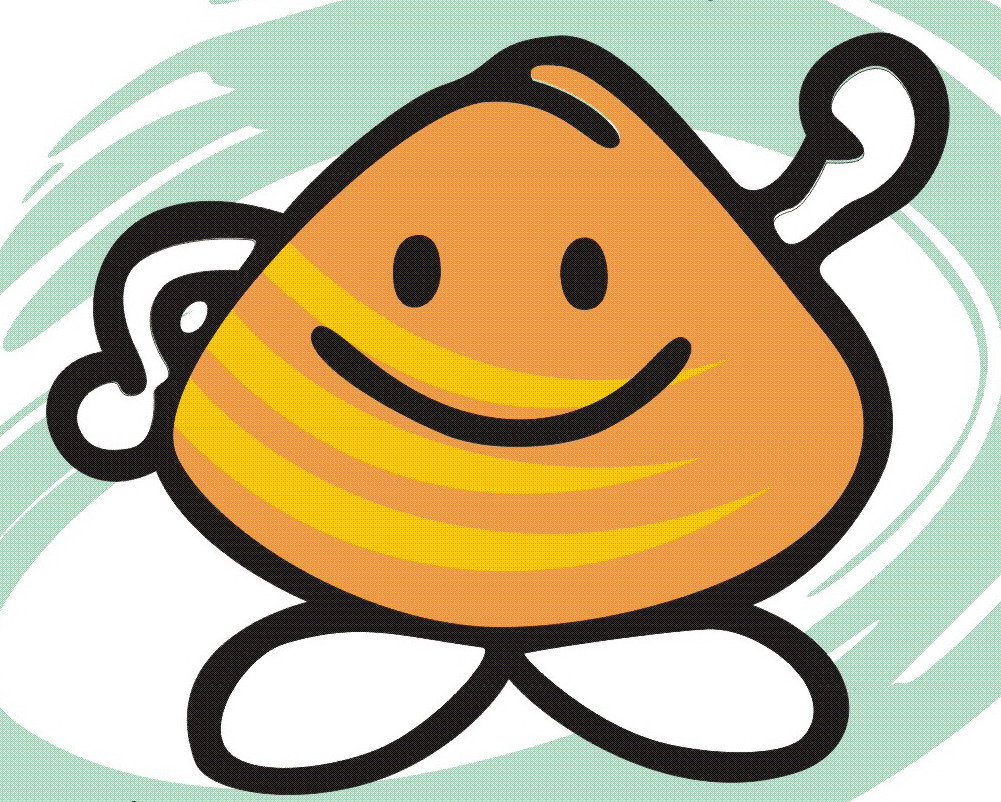- 今日人數:6
- 累計人數:25910
- 發表文章:18
- 相片數量:20
- 回應數量:1
- 網友按讚數:0
 2014/12/17 20:16 | 社區風華
2014/12/17 20:16 | 社區風華從離散到新住民
李冠廷
距離第一批的墾員來到這裡,已經過了十多年。當時沒有配偶的,現在幾乎都已成家。懂事的孩子為了讓家裡的生活能過得好些,已經到外地去工作。傍晚的巷口,此起彼落的孩童嬉鬧聲漸漸褪去,只見著低矮的平房裡頭點著燈,裏頭的人們正談論著農事之後還有哪些工作好賺零頭。
張春清收到入伍通知令的那時,已經在外頭工作了好一陣子。十六歲初中畢業之後就離開家鄉,隻身前往外地工作掙錢。一個來自花蓮的年輕小夥子,去到桃園的大型機木場工作,要先經過考試測驗,通過後還不能直接上工,還要先上課,直等到基礎訓練完畢之後才開始正式工作。工廠裏頭傳來大型機械運作的陣陣聲響,外頭則是堆滿了來自各地的木頭,有的硬,有的韌,有的新嫩,有的陳舊。這些木頭就像是這工廠裡來自四面八方的工人,有著不同出生背景,但此刻卻都聚在一起。工廠發給每人一套制服,質材粗硬,但終究是體面,也經得起木材在衣服上任意磨損。制服上用楷書繡著三個字:技術生。
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底下,工作賺錢是第一目標,讀書則是次要,這點在張春清的童年深有體會。即便學業成績優秀,但身為長子的他,必須肩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,升學進修的念頭只能在年幼的腦袋裡空轉,沒有機會實現。要升上初中之前,他瞞著父母去報考空軍幼校,只要考進去後,未來就有機會進到空軍單位服役。考完試的那天,他是踏著自信的步伐離開考場。照理說應該要寄回家裡的成績遲遲沒有下落,他想著說可能是自己名落孫山,雖然無奈,但還是依照家人的指示去到一般初中。當兵退伍回來之後,他向父親提到這件事。當時跟自己一起去報考空軍幼校的朋友,現在已經是尉級軍官。只見父親默默地搬出樓梯,在屋頂中的夾層中搜索,翻找出一張早已破舊泛黃的紙,那是張春清當時報考空軍幼校合格的通知。「當時不是不讓你念書,但你是長子,假如你走後,就沒人可以分擔家計。」見老父親一邊嘆氣一邊說,自己心裡是感概也是安慰,感概是大環境迫使他必須放棄這大好機會,安慰是原來自己能力不比別人差。
俞東英初中之後就離開村子,遠到桃園的復興紡織廠工作。她是墾員俞桂春的女兒,在台東卑南鄉出生,之後全家就搬到共和村定居。在村子裡長大的她,在木棉吐絮的日子收採著棉花,在涼爽的午後和同伴在院子裡跳繩,村子跟著她一起長大、變化。離開村子後,到了紡織廠做成衣,在台北當過欣欣客運的車掌小姐,也去到梨山的農場做過餐飲。之後,她結了婚,對象是同樣在共和村長大的呂南山。可能是來自同一個地方,同樣的生長背景,她和先生之間有份不可言喻的親切與熟悉。從娘家到婆家,僅隔了兩個街口,不到五百公尺,走路便能抵達。結婚後沒多久生下了老大,但因為先生要去到台南工作,便將兒子託給婆婆照顧,自己便隨著先生到了南部去打拼。隨後又生生了兩個男生,但是因著工作的緣故又搬到了屏東,同時也將就小學三年級的大兒子接來屏東,這時才真的是全家的大團圓。
先生後來被診斷出肝癌,且已經開始有擴散的跡象。命運的安排似乎總是乖揣巧妙。在得知先生患有肝癌的不久之後,年歲已高的婆婆竟先逝世,老家裡只剩下公公尹思昆一人。曾在門諾做過護士的大姑姑建議東英他們回到花蓮,黃勝雄開刀治療。礙於當初交通不便,先生的病情又不容長途跋涉,便坐飛機,從屏東直奔花蓮。無奈在開刀之後,病情仍沒有好轉,在回到花蓮幾個月後便撒手人寰,和母親到另一個地方相聚去了。
遭遇如此不幸,生活還是得過下去。幾番商議之後,俞東英最終決定回到共和村居住。一方面三個兒子都很獨立,不需要她操心;一方面可以就近照顧公公,讓他不是孤單一人的生活。相較於大都市的繁榮,留在村子裡或許不是最佳選擇,但在這彷彿與世無爭的鄉村裡,又是自己長大的故鄉,就這樣休閒自得的生活其實也不壞。
這些年來,許多人離開了共和村。或許是為工作、為了更好的收入,或是冀望更好的生活,共和村原來的居民開始遷出,有的人在年節時還會回來,有的索性把土地賣了作為到北部打拼的基金。賣掉的房子、土地,有的人去樓空,有的則是換了新主人
楊國望原本和朋友集資要在花蓮這裡做養殖魚買賣,但礙於當時壽豐交通不便,魚賣不出去,只好作罷。他是陸軍特種部隊退伍的,跳過傘、打過各式演習,還去到美軍的潛水艇中實習了好長一段時間。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他,心中的意念就是忠信,因著朋友的一番話,他便取了一大筆錢,從新竹翻山越嶺來到花蓮。當初投資養魚的錢是向朋友借的,為了抵債,只好一邊做工、一邊養魚,自己的退休俸拿來還錢,家裡的生活則倚賴做工所賺取的微薄薪資。「既然來了,就不後悔。」太太楊朱綿從新竹跟著先生來花蓮,一轉眼就過了二十個年頭。
其實剛到花蓮的前幾個月,楊朱綿很不能適應這裡的生活。結婚後是住在現代化的水泥房舍裡,有電有水,生活很是方便。突然搬到花蓮鄉下的農村,生活的水平還是有些差距。他們夫婦剛來到村子裡,是住在當時的墾員毛聯富租來的房子裡頭。說是房子,其實不過就是多出來的平房,旁邊還緊鄰著豬圈,只要一下大雨,豬糞就會溢流滿地。剛來到村子沒幾天,還碰巧遇到大地震,震央在瑞穗,將近七級的地震,晃得讓人站不直腳。這些種種經歷讓楊朱綿很不能適應,整天傷心流淚。,
楊朱綿搬來的行李很多件根本沒有拆封,心裡還盤算著:「什麼時候時要離開這個地方?後來經過好長一段時間,夫婦倆才漸漸適應,並且在農墾一街那裡買了地,蓋起了屬於自己的屋子。
對共和村的村民來說,楊國望夫婦像是外人,畢竟東西部的生活型態還是有差異,對生活的要求各有不同。不過相處在一起久了,也就漸漸接納彼此的生活。最先表達出善意的,是當時的村長尹思昆先生。他和楊國望都是湖南人,同鄉之間總是比較好聯絡情誼,也就催促著他們夫婦,趕緊在村子裡置產,安定地住下來。
尹思昆在民國四十九年時結婚,太太徐阿桂是在原來的丈夫去世之後,,帶著四個小孩改嫁給他。雖然這四個小孩不是自己親生的,但尹思昆仍然當他們是自己的小孩來教養,自己和徐阿桂也就沒有再生小孩。
他過去練過武術的尹思昆,對治療跌打損傷很有一套,當村子裡的人筋骨痠痛、瘀傷脫臼時,就會來請他治療,而他也從來沒向村民收過半毛錢。每當有活動節慶時,他也會應大夥的要求,上台去表演幾段武術。只見他身手矯健、拳腳來勁,歲月的痕跡在他身上似乎並不明顯,年過半百還是虎虎生風。
久而久之,村民對有俠客身手的尹思昆頗有好感,之後便推選他做共和村的村長。雖然擔任村長不會增加多少收入,但能為村民服務,他是義不容辭,而這村長一當就當了十多年。
因著有幾個同鄉的幫助,加上對壽豐這邊也愈來愈熟悉,楊國望夫婦漸漸地就融入了共和村裡頭。他們的房子蓋在農墾一街,門口望出去就可以看到鐵路以及壽豐村,再遠眺過去就是綿延不絕的中央山脈。那時楊國望雖然已經退伍,退休俸半年領一次,但為了償還當初蓋魚池的債務,還是去兼了好幾份工作,不論是鋪馬路、做空心磚,這些事他都做過。一個從特種部隊退伍下來的軍官,卻是做這些粗重的苦工,這讓以前在軍中的同袍們看了很是不捨,便介紹他到後備軍人的輔導中心擔任秘書,這樣一個月至少有七千元的收入,也可以免去在烈日下幹那些粗活。「這些故事不僅僅是歷史,還是奮鬥史。」在提及過去的回憶時,楊朱綿臉上總帶著一股堅毅的神情。她提到當時為了養殖鯉魚需要用動物糞便做飼料,但家裡沒有養豬,只好沿街撿拾豬牛大便。那時楊國望會拖著一台輪車,太太和兩個小孩一邊撿拾糞肥,一邊往輪車上堆。「那時候我們都是這樣苦過來的。」楊國望輕鬆地說道。
當時村裡的對外道路不多,最快到達壽豐火車站的便橋就在楊國望的房子附近。村子火車站中間隔了一條樹湖溪,如果走一般道路,有時要個半小時以上,但如果走便橋,只需十分鐘就能到車站。其實那也算不上便橋,不過幾條鋼索連接,中間鋪上木板,僅能讓行人穿行,但也省去不少來往壽豐街上的時間。
共和村裡的小孩要上課,多半都是走這條便橋。下了課,天氣炎熱的午後,橋下的樹湖溪就成消暑的游泳池。便橋離水面有一段高度,但溪水夠深,於是常有孩子從橋上一躍而下、涮的一聲落進水裡,濺起了高高的水花。墾員第二代的林家根就說道,樹湖溪不僅是當時孩童們的游泳池,也是天然的澡堂。除此之外,溪水裡的魚、蝦若是大意被逮住,就會成了孩子們加菜的食材。後來台鐵認為行人這樣私自穿越鐵道太過危險,又剛好遇到河堤修整,那老舊的便橋就遭到拆除,舊有的風貌僅留在那些踩踏過的村民心底。
楊國望夫婦搬來共和村之後,陸陸續續有許多人也遷入村子裡。何秀蘭本來就是花蓮米棧人,後來結婚嫁到溪口,民國八十一年才又和先生搬到共和村來。之所以會選擇共和村,一方面是這裡的生活比較單純,另外離壽豐火車站也近,生活機能也足夠,就決定在這裡定居下來。此時村子裡的建設已經比較完善,從過去的泥土路變成柏油路,路旁的水溝也加上水溝蓋,雖然比不上壽豐大街,但社區生活也已經有很大的改善。而最近一批的「新住民」則是遠離塵囂的都市人,王新雨來自台北,趙振榮則從高雄來,都打算過個退休的隱居生活,也為村莊帶來不同的風景。
王新雨本來在台北的外商公司上班,但自己的小兒子身心有些狀況,不容易與外人相處,於是就想著退休後要好好照顧兒子。王新雨的太太是花蓮人,家庭出遊時也常往東部跑,對花蓮這裡的狀況也還算熟悉。看著自己的小孩,王新雨有了個念頭:為何不在花蓮找塊地方,讓一家人平靜的過生活呢?民國九十六年退休時,先是在花蓮豐裡買了一塊田地,預備說退休之後可以自己種植作物。接著就開始在花蓮各處看房子。最先在美崙看,雖然有不錯的地點,但沒有院子,這讓他太太有些失望。後來陸續往南,吉安、干城、南華,雖然都有不錯的地方,但不是價錢太高,就是欠缺穩妥。為了那未來理想美好的願景,夫婦倆仍耐著性子繼續地尋找。
「這似乎都是冥冥中緣分就註定好了。」民國九十八年,誤打誤撞進到了共和村,看到了現在住的房子。原來的屋主並沒有細心地保存房屋,整間平房爛爛舊舊的,但王新雨就覺得這個地點很好,也沒有想太多,就買了下來。後來經過一番裝潢修飾,一些地方打掉重建,花不到兩百萬就原本的舊農舍改建成新式平房。
之所以選在共和村,一部份是因為這裡還有鄰居,遇到甚麼事還可以有個照應,加上離壽豐火車站也不遠,民國九十八年的元旦就帶著妻小住進了共和村。
王新雨搬進來三年後,趙振榮也跟著搬進了共和村。趙振榮原先就是花蓮人,長大後念了軍校才離開花蓮,接著在軍中不停調換部隊,最後是在義守大學擔任教官時退伍。結婚之後,民國七十八年就在岡山那裡買了房子,只是當初買的是公寓,住一段時間以後覺得不是很滿意,想要再換個地方。「找一個終極目標來定居。」趙振榮和太太商議之後,決定找一個最合適的房子,當作退休養老的地方。
民國九十四年從教官職任退休後,趙振榮就開始四處看房子。因為老母親在花蓮,自己也覺得東部的環境比較適合居住,便利用空閒的時間在花蓮找房子。偶然一次知道壽豐這裡有房子被法拍,便循著地址找到了共和村。雖然從小在花蓮長大,但也不可能每個地方都去過,而這次便是他第一次進到共和村。經過了幾番輾轉,終於在村子裡找到了落腳之處。待新居完工之後,全家人便從高雄搬到了共和村,開始了新的生活。
王新雨和趙振榮這兩位新住戶搬進共和村之後,開始做了很多關於社區發展方面的工作。王新雨在民國九十八進到共和村之後,便到了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工作。因工作的需求,他去到了花蓮許多鄉鎮,也看到那些地方的社區活動是如何運作。當時在養殖協會的王博瀛對王新雨這樣的新住戶很有想法,希望他們能夠給村子帶來更好的發展,便鼓勵他們能對共和村有所回饋。幾經考慮之後,王新雨答應接下這項任務,用之前在工作上的經驗,開展在共和村的社區工作。
「我們的心態就是:住在這邊,就融入這邊。」趙振榮說道,假如村子有需要、自己又有能力,為自己所住的社區付出並不會有損失,假若這樣的付出可以促進社區的和諧,那就值得了。當社區發展協會有工作分派的時候,趙振榮總是義不容辭地接下,不論是社區樂齡班的課程還是關於社區發展的提案,他都全心全意地投入。但他也提到,假如社區發展裡頭沒有一個產業可以吸引人,那社區的凝聚力還是不足。尤其是在鄉下農村這種地方,不僅要留住年輕人,還要吸引外地的人進來,那真的是需要經營一些具有發展力的產業。
共和村是一個有歷史的農村,只是村裡頭的人來了又去,去了又來,第一代的墾員多半都不在了,剩下的第二代也僅有少數留在村子裡,再來就是外地來的新移民。假如都沒有人關心社區事務,那整個村莊將會變得冷漠沉悶。
王新雨和趙振榮他們倆位都不是本地人,不是土生土長的共和村民,不是墾員的第二代,但他們卻深深的認同這塊他們生活的土地。王新雨接下了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的職分,但在還未擔任這職分之前,他已經在村子做了許多事情。在他看來,不論有沒有這個名分都沒有差別,任何人都可以為著社區來盡一份心力。除了自己以外,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認同、並投入共和村裡頭,一同來從事社區發展的工作。目前有一群大學教授打算移居共和村,已經在村子裡頭買了地、蓋了房子。假若這些新住戶也能一同來建設共和村,相信能給這個老舊的農村帶來很大的翻轉。
新住戶投入社區工作,就像是給村落注入了一股新血,同時也帶動了整個社區的發展。往後共和村會有怎樣的發展,令人充滿期待。
消息來源:
張春清
俞東英
劉(林)家根
楊國望
楊朱綿
王新雨
趙振榮
尹秋明
黃淑燕
何秀蘭
個人簡介:
李冠廷,來自高雄市,卻始終認為自己是個叢林來的野人。皮膚被南部的太陽曬得黝黑,到東南亞的幾場時會被投以親切的笑容。喜好烹飪,但常把鍋子燒焦;喜好攝影,但不時讓底片過曝。從事新詩、散文以及歌詞創作,作品風格風格慵懶而淺白。目前正在東華大學華文系攻讀碩士。
後記:
做了不到一學期的觀察採訪記錄,卻也讓我心力憔悴。採訪報導並不是有問有答的直向對談,有很多說不出的片段需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追尋。有時問題不夠精準,得出的採訪就不精彩;關係不夠熟稔,得出的記憶就不夠親切。在採訪的過程中,我感受到了這個村子的溫暖。村子裡的人們,知道我們是學生,便時常關心我們的生活、學業。有時採訪得晚了,便被留下來用餐,甚至還帶了許多免費的菜餚回去,讓我節省了好幾餐的飯錢。即便去採訪不在村子裡的人,問到村子過去的事,他們也是熱切、積極地談論,並沒有當我是外人而有所保留。我喜歡聽故事,尤其當哪些經歷豐富的人們,談及他們過去的豐功偉業時,我會變得興奮而激動。這次的採訪紀錄中,美中不足的是時間太短,感覺還有很多細節沒有挖掘出來。假如下次要再從事採訪活動的話,「蹲點」將是我要努力學習的部分。
 2014/12/17 20:12 | 社區風華
2014/12/17 20:12 | 社區風華〈落土新生〉
樹湖溪水緩緩滑過村子,水鳥步行在水中,漁人佇在堤防釣魚,黑腳黃襪的小白鷺正飛過溪流上空。溪水將與北邊的荖溪相接,匯流藏身於養殖水塘區的花蓮溪,水更外流,溪岸愈寬,一整面灰白的河床地,鵝卵圓的石頭,夾雜著藍綠的水色,一路蔓延挨近海岸山脈,沿著山,溪水流入散著粼光的太平洋,與村裡老人記憶中渡海而來的黑水溝,是完全別樣的面貌。
圍繞在村子周遭一大片接連的土地,正巧有村人耕種著,種些自家食用的芋頭、地瓜葉及玉米,不做販賣之用,不灑農業。有些地剛割完草,八哥鳥趁隙在田間啄食,有些地有秩序地排列種植香蕉,有些則種植高麗菜,而絕大部分生養著芒草、大花咸豐草,以及小花蔓澤蘭這類型的雜草。這些地散落在村子裡,有的是祖產,有的是村人後來買的,有些可能是地方最大地主花蓮農場所有,有些則是村人從未見過,遠在台灣某處的不知名人家買下的。
沿著樹湖溪錯綜複雜的橋墩,能走進農墾街道。
村子裡有點小騷動,人們正討論一場「過年的活動」,打算在新年期間,把居住在外地的那些舊居民給找回村裡。節日是村子重要的意涵。逢年佳節,離鄉背井的年輕一輩,都會在此刻回到村子探望老父母親,以及兒時生活之地。
村人們總是各自來到,村子已經有段時間沒有辦類似的聚會,有村人想趁此時,把大家找回來一起熱鬧熱鬧。
「過年喔,就是大家聚在一起,那時候還有送老人家禮物的。然後辦桌什麼的……」村人黃淑燕回憶那段時光,顯得有些模糊。
「我記得兩次,一次是年輕人聚在一起,在活動中心那邊,大家吃吃糖果什麼。還有一次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人參加。」村子裡的老家長,大家喚他楊媽媽的楊朱綿也隨之聊起舊事。
距離上次的聚會已是許久之前,人們只是模糊記得還誰參加過,一群人聚在一起唱唱跳跳,聲舞盡歡。一場正在安排的聚會,正挑動著大家的心思。
從農/初生
鄰人們正聊著過年的聚會時,錢世保家中的庭園還曬著高麗菜乾。高齡八十六歲的他已經少去自己的農地耕種,把地託給別人照顧,自己只是在庭園用保麗龍箱做起簡易菜園,種些長起來還比他頭大的高麗菜。裸著上身的他胸口隱約有著在中國與日本人打仗留下的彈痕,而腳上與股側在作戰時受到的刀傷,顯然沒有成為他走路的礙事。
年輕時的錢世保活躍在一片河床砂石地裡。當時不是現在的光景,在他來之前,匯流至花蓮溪前的這幾條溪流,木瓜溪、荖溪、樹湖溪,以及那些從未被命名而兀自逕流的溪水,將這片土地聚攏成一座石頭打造的自然荒地。
民國四十八年,他輾轉來到村裡,剛到村子時有眷屬的可分地一甲三分,單身的則六分。錢世保得地六分。
他曾站在一片河床地上,當時稱為「開發區」。河床上的人們一個個擔著扁擔,兩邊的竹簍沉沉,低頭挑石挖地,不斷重複的動作著。一夥人穿著白色汗衫,深灰色的褲子捲至膝蓋,戴著乾竹葉做成的斗笠。有些人耐不住熱,乾脆裸身涼快,穿一條白短褲便開始搬搬抬抬,任由汗水滴落石上,讓烈陽曬成痕跡。
那裡一顆顆比人的胸膛還大的石頭,還藏著比錢世保雙手圍掌還大的蛇。人們將高處的石頭拉到低地墊高,用石頭堆起田界,還得從其他地方運來土壤,才得以插秧種植。河床多石,當時村子裡還有不少房子用石頭堆砌而起,而今已經已不復見,更遑論那些久未耕作而還給花蓮溪的田地了。
烈日照在花蓮溪的這一片石地上,錢世保、俞桂春與陳宙然,以及其他來到村裡墾荒的墾員們,他們從台灣海峽彼岸一路顛簸而來,褪下軍服,成為初生而未熟的新農。溪水反射的陽光射進他們的眼睛,像是第二個太陽,汗光粼粼,在海岸山脈回返的熱風裡,曬成一個個閃耀的黑石。

錢世保在自己後院種著高麗菜。
「以前都是爛地。」錢世保說:「種什麼都不活。」而種不活的土地養大了兩兒兩女。
大兒子錢新南在一百零二年退伍,同他的父親,也是一名軍人。定居在台北,逢年過節有空便回到村子探望老父親與故人。他是農村社會眾多小孩的一名。農村社會裡,小孩要生得夠用,要比耕田的牛還多。村子裡小孩都跑來跑去,跑在田隴間,跑在不似今日柏油路的砂石地上。通常下課就要回家幫忙農事,周末上課只有到中午,還要等爸媽回家才有飯吃,放假就得幫忙做農,不能亂跑。
錢玉南,錢世保的二兒子,他在村裡已有很長一段時間,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。還記得每日下課都得乖乖回家,如果遲到了沒去幫忙,要被父親罰跪在田埂上,跪著一雙腳都黑青發疼。家裡以前種些青椒、辣椒,一雙手採得紅辣辣的,洗了好幾次沖不掉辣意,晚上還會發疼。那時候村子裡的大人怕小孩跑不見,把小孩抱去田裡,做事前還要用一根粗麻繩把小孩繞在樹下。錢玉南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被綁過,但他看過其他小孩被綁在樹下。
瓜果類是村子種植的共同記憶。共和村有些地富水,適合種稻,適合挖開養魚,也拿來種西瓜。錢世保還記得以前種西瓜,種到快收成前如果來一場雨,那西瓜肯定因吸水而壞去。有次趕在下大雨前把西瓜全部摘一摘,摘不完的,還打電話給當初說好契作包農的商人道歉,全然看天吃飯的生活。而曾經最辛苦的,莫過於種植棉花,摘棉花需要相當多的人工,卻是能夠賺錢養家的作物。錢世保沒有雇人幫忙,一切自己來做。
村裡有些人家種植水稻,收穫時節找大家會一起幫忙,「今天幫忙我家明天幫忙你家。大家都沒有在分的。」錢新南懷想起以前農忙時,鄰居還會用麵粉和著蔥煎成厚餅,彼此分食感謝。過年時家戶做些年粿,一群小孩圍著看大人在灶上煮米漿,水份蒸騰灶腳,大夥笑鬧,小孩幫忙攪拌米漿免得燒焦,越攪越累,黏得像是村人的緊密感情。
過年時孩子都已經放假了,如果學校沒有放假,便會聽見壽豐火車站員大喊:「別別別別──」錢家兄弟與他的鄰居朋友們,時常直接穿越火車鐵軌,到家對面的壽豐國小上課,一邊奔過鐵軌,一邊大笑。「這樣比較近嘛,也不用錢。」錢新南如是說。而他手指的那個地方,至今已是一片草堤。
孩子就像作物一樣地長大了,牛消失了,孩子也都離鄉了。

錢新南(左)、錢世保(中)、俞桂春(右)在午後聊起從前的生活。
鬧水/流轉
俞桂春記得當初到台灣的退伍軍官,有些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颱風,在村子裡第一次遇上颱風,自己的房子雖是蓋著鐵皮,但還是抱著孩子趕緊到鄉公所等待風雨過去。但他的好友錢世保,跟村子大部分的人還都是茅草屋,外表看起來很美觀,風一來,屋頂刮走都不知道要去哪找了,修修補補了好幾次。有些人沒辦法生活,乾脆離開村子。現在生活在村裡的人,都經歷過修補房屋的記憶,能夠留下的也是經過一番風雨。
颱風是村人的共同記憶,也是村子裡的大事了,家戶動起來把家裡整頓安置,深怕又讓屋頂給吹走了。颱風鬧水,村子落在兩山之間,河溪匯集之處,地屬低平,時常水災,逢雨必淹。可鬧水是村子小孩最快樂的時候,水患及膝,小孩便會跑出家門到街上給家裡加菜,跑在雨中跑給風吹,踏在街道上一圈圈的水花,到處追逐免費的魚,那些溪裡游出的魚,水塘裡流浪的魚,追到成為肚裡的魚。這或許看在曾經養魚的楊國望與楊朱綿這對老夫妻眼裡,心情可是好笑又複雜。
村裡在農墾街道周圍多是農地,居住在農墾街的村民多半務農。而在村裡更向外圍,越靠花蓮溪處,一畝一畝的藍色土地,都是養殖魚塘。楊家倆老的養魚記憶,也是共和村共同的境遇。早在立川漁場坐落於地方成名前,村人以漁業為生。彼時是民國六十年代,政府推動三合一農漁牧政策,當地也有不少人開始做起綜合農業,養豬養魚維生,豬的糞便可以給魚,魚吃豬消化未完的飼料。
民國六十一年他們來到村子時,土地已由錢世保、俞桂春這樣的開發隊築好了。他們用三萬四買了一甲多的土地,自己往下挖深一尺,水便汩汩冒出,是活泉地,相當適合養魚。當時一斗米約六十元,一天的零工也才六十元。倆老是倚靠著楊國望的退休俸,一邊打工一邊還債,花了十年才還清買地的錢。他們在魚塘養了鯉魚、草魚,長得很好很肥,多到分送給鄰居。吃魚吃到怕了,拿著大草魚跟人交換蘿蔔乾。原本想要向外地販賣,當時壽豐一帶交通卻不便利,無法像農作物一樣送到更遠的地方賣,過沒幾年,就乾脆把地收了,不做了。後來賣掉的土地,如今已水漲船高。憶想當初賣地,楊朱綿百般難過,心有不捨,還記得賣地給一位姓張的人。賣地之時,兩人還在推託,對方說要先收下定錢,但楊朱綿不願收下,心有掛念。
「畢竟是自己的。」楊朱綿平淡裡仍帶著感慨地說著往事;「要不是孩子大了,做不動了,也不會賣。」
「我看你收下訂金,我才安心了。」楊國望回憶起當時他們手捧著錢,穿過一分一甲泉湧活水之地,走到天黑了大半,才悻然回到自己的家。過沒幾年,立川漁場買下那塊地,而今已漲成是富甲之地了。
在社區養殖協會的紀錄裡,現今村子的養殖區大概四百五十公頃,約莫有七十幾戶的養殖戶,大多是五六十歲的人居多。他們多半是當地人,不像是村子農墾街裡是退伍軍官居多。然而遇上的問題,卻同樣是年歲高邁,後續子女不一定會接下家業,甚至奔走他方。有些漁民不如就把地賣了,賣給立川漁場續作養殖,或是跟漁場互利,託給漁場幫忙販賣,讓自己還可以活在土地上。
清晨與午後近晚,他們會在太陽日昇日落前的時間在魚塘工作,閃避一如彼時墾員艱辛墾荒,水面上的另一個太陽。
水很熱鬧,村子像是在水上浮載一般,因水而生,亦患於水。先至者如錢世保一輩在河床地上墾荒,成就一畝畝的農田水地,成為村人維生的農業與漁業。滄海桑田,幾經變更的地貌成為現今在農墾街一只告示牌上的地圖模樣,一面空照的全景圖,懷藏著已久的歷史。這個村子脫離不了石頭跟水,整座村子就是活在水上的。

與楊朱綿邊走邊聊以前的生活。
販土/落生
每塊土地都擁有身世,而擁有土地的人將會寫下土地的歷史。
錢玉南曾笑說:「過年過節才知道共和村人很多。」然而談起共和村這些年來的人去樓空,從事土地買賣事業的他倒也收起笑臉,換了另一副嚴肅的面容。村子大抵在民國七十五年到八十五年賣地最甚。現在村子不復以往,以前大夥兒一起在農收時節合作收穫的情形都留存在記憶裡了。村子裡剩下比較年長的一輩,大部分的土地多半留著不耕作,就是放著領休耕補助款,若不忍心曾經辛苦過的土地變得荒蕪,就乾脆交給別人去做好了。
土地一但傍身,情非得已是不願放去的。

錯落的遺址,散失的人,留下一只門牌,還有一棟空屋。
「那些地主都不認識,也沒看過。」村人黃淑燕看著一整塊蔓生雜草的土地如是說著。民國八十九年農業發展條例通過,購買土地不再限制於自耕農,許多外地的人在村裡買地置產,或隨意種植些作物等待蓋起農舍。花蓮的土地價格上漲,錢玉南說壽豐這裡更漲,共和村近一二十年翻了幾倍。除了外地人買來置產,等待蘇花高的開通,等待周圍土地開發案起,等待土地增值,其中不乏相中共和這塊水質寶地的外來廠商,有意開發,要來種植藥草。
買賣農地是門技術。用來置產的無非還得看是不是重劃區,有沒有開發計畫,牽涉著地形,甚至是與附近周遭道路的距離。諸般考量,農地像是半成品,必須養地卻不種植作物,等待半成品的熟成需要時間,而這段時間任由著土地荒生。
農耕是門學問。在村人的記憶裡,河床地育養女子長大,成為生活的命脈。而沼地種植不易,收成較差,也成為村子既定的印象。村裡老一輩的人無法耕作,年輕人遠走他鄉,這片河床地被放棄了,成為母土成為棄子,成為時代流轉的印記。村子不像以往這樣大規模的耕作,有些村人想是倒不妨賣出土地,還能過十餘年的小日子。村裡土地仍有所種植,多半自食而不以販賣維生,像楊朱綿、黃淑燕,以及一些村人的家裡都有農園,種些蔥菜養些鴨鵝,過簡單自足的半農生活,交換彼此作物。
也或許如此,村人對於「過年的活動」有著別樣的想法吧,復歸的人們成為村子轉變的見證。
販土也許是時代驅使著人們放棄所有。錢新南提到那些曾在家裡周圍,與自己同樣長成的兒時玩伴都不知道去哪邊了。有些長輩過世之後,遠赴他鄉工作的孩子回到地方,將土生土長的土地賣掉後,從此再也不見其影。有些地啊人啊也是語焉不詳了。
而買土的人也或許是落土新生的一代。「這一戶也是新來的。」楊朱綿對著一戶新砌水泥白牆的房子說:「太太好像滿喜歡玫瑰的,買了很多來種。」錢世保也曾對著這戶新鄰居善意地問:「今天禮拜幾?」新鄰居不明所以,有些驚喜地回應著錢世保的問句,伸出五個手指,禮拜五。這戶新進村裡居住的人家,在村裡買了塊農地,正巧在錢世保農地旁邊。
時間正流轉,村子也正變換,販土的人已經不知去向,而落地於此的人會再生根,如同共和村座落在水與石頭之上,水仍流動著,人將延續。
資料來源:
養殖協會/立川漁場:蔡國華、洪偉誠
共和永續發展促進會:王博瀛
共和村民:楊國望、楊朱綿、錢世保、錢新南、錢玉南、黃淑燕
參考資料:
胡台麗《石頭夢》
退輔會《農場老兵文學》
個人簡介

吳金龍,1988年。
現就讀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班創作組。大學讀於山城埔里而喜歡山,現居花蓮依海而喜歡海,大抵一生脫離不了山海。
後記
我記得是下午兩點,與幾個同學在村裡晃盪,突如地加入一夥村人的聚會之中,記得是在張來善大哥家裡。那時候聽到許多訊息,像是點狀般還讓人摸不著頭緒,當時令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「過年的活動」。村裡對於「過年的活動」有不同的記憶與想法。對於一個外來人如我充滿想像,對於這個事件,能夠有多少人回來參加,拼湊屬於地方的圖像。時間在流轉,共和村成為歷史的見證,從日治時期壽豐製糖,到國民政府來台安放退休軍官墾荒,而今土地猶存,人事漸失,村子又正在轉型,成為另一種圖像。
我曾問過村裡的大事是什麼?這是個不好的問句,應該說,村裡什麼事情最令人印象深刻,是鬧水災。鬧水是共和村坐落在花蓮溪的最佳地理證明,活水區上的人們依水而生,因水而苦。在水上的共和村,早期的墾荒、農業,乃至於養殖,觀光,在流轉的軌跡裡人來人去,這些都需要被記錄,成為時代的印記。
在村裡行走,也許感觸最深的莫過於土地的棄置,也樂道於村裡的小農園。這讓我想到「土地從何而來」。如果說人是自然裡的居民,那人們什麼時候開始與土地共生,再把土地珍視為財產,而後甚至成為買賣的物件,土地從什麼時候限縮成人們口中的一個名詞。行走於村裡有主人而無人耕作的土地時,總是想起這些大哉問,抽象的形而上。
然而人們正在土地活著,以各種形式。人們會記住自己在土地上的記憶,而
土地會留下人們生存的痕跡。
| 共 14 筆 |
|